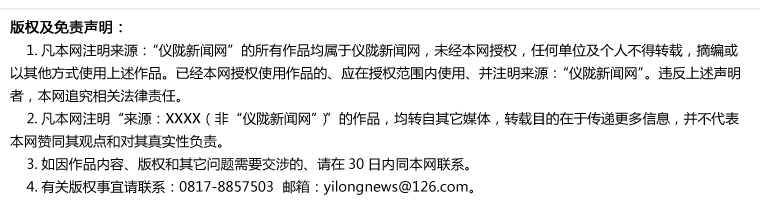本網(wǎng)訊( 余劍 吳曉菊)在偏遠(yuǎn)的村小,他一呆就是36年,將人生最美好的時(shí)光給了山村的孩子。
王家店村小離度門鎮(zhèn)約3公里路程。如今,這個(gè)村小只有11名學(xué)生,從幼兒園到一、二年級(jí),最小的孩子4歲半,最大的還不到10歲,絕大多數(shù)孩子是留守兒童。
學(xué)校既是何學(xué)文的家,家也是他的學(xué)校。他要教學(xué)生所有課程,還要保障學(xué)生上學(xué)、放學(xué)路上的安全,最遠(yuǎn)的學(xué)生要走3公里的山路來上學(xué),不論天晴下雨,他都要接送學(xué)生。
“我在這個(gè)村小呆了16年,舍不得離開這里,如果我走了,這些孩子就要到南部縣的石河小學(xué)去讀書,路途更加遙遠(yuǎn),這對(duì)四五歲的娃娃來說,幾乎不能承受。”望著這些天真無邪的孩子,何學(xué)文說,“這些孩子的父親都是我的學(xué)生。如果上面批準(zhǔn),只要還有一個(gè)學(xué)生,我還是愿意留在這里,直到教到走不動(dòng)的那一天。我常常告訴這些孩子,只要努力,就一定能走出大山。”
盡管送走的學(xué)生一批又一批,來村小教書的教師走了一茬又一茬,不變的,是這個(gè)村小有個(gè)老師叫何學(xué)文。
“我教過的學(xué)生,有一個(gè)正在清華大學(xué)攻讀博士,光研究生就有7個(gè)。”何學(xué)文滿臉自豪,“每年生日的時(shí)候,很多學(xué)生都回來看我或打電話送上祝福。”
1976年,何學(xué)文從南部師范學(xué)校畢業(yè),曾在度門鎮(zhèn)的先鋒村小等地當(dāng)教師,1996年回到老家,擔(dān)任王家店村小教師。
他到王家店村小任教沒多久,一場(chǎng)罕見的大雨使本就破舊的校舍成了危房,村委會(huì)組織村民集資建學(xué)校,由于經(jīng)濟(jì)落后,相當(dāng)一部分村民都交不出50元的集資建校款,修建學(xué)校一事就這樣擱著。看到全校師生每天膽戰(zhàn)心驚地在危房上課,遇到吹風(fēng)下雨,就只能在這家屋檐,那家院墻下躲躲,他與妻子商量,拿出準(zhǔn)備給兒子結(jié)婚用的4.5萬元錢來修學(xué)校。
他在自家自留地建起了3間教室,從破舊的老學(xué)校搬來了桌椅板凳。到了第二學(xué)期招生的時(shí)候,學(xué)生猛增到118人,桌椅不夠用,他又拿出準(zhǔn)備給兒子做家具的木材,給學(xué)生做了30套桌椅。
“每天中午,學(xué)生都是三菜一湯,經(jīng)常換著不同的口味。有幾個(gè)太小,不太吃飯,很多時(shí)候,都是我和老何給他們喂飯。”說這話的是陳桂芳。何學(xué)文的前妻去世后,陳桂芳成了他現(xiàn)在的妻子。
去年9月,為學(xué)校孩子義務(wù)煮了15年飯的何學(xué)文的前妻因患肺心病離開了人世。前妻去世后,學(xué)生的午餐就只得由何學(xué)文來做,又要獨(dú)自一人教書,又要獨(dú)自一人照顧學(xué)生生活,顯得特別辛苦。一些鄉(xiāng)鄰看在眼里,就為何學(xué)文介紹了喪偶又曾從事過廚師行業(yè)的陳桂芳。
“何老師是一位重情義的人,前妻就安葬在學(xué)校的后面,每當(dāng)休息時(shí),他總在窗子眺望,看著他濕潤(rùn)的眼眶,我心里也非常難過。去年,給前妻買了一部手機(jī),至今還放在家里收藏著。”為了讓何學(xué)文減輕傷痛,陳桂芳接過他前妻的接力棒,義務(wù)為孩子做午餐。陳桂芳一邊與筆者擺談,一邊在菜園子勞動(dòng)。她說,得多種些小白菜,孩子們每天才有蔬菜吃。
按照規(guī)定,今年7月,何學(xué)文就要退休了,村民都不愿意他退休。何學(xué)文說,為了能讓山區(qū)的留守兒童有學(xué)上,他會(huì)繼續(xù)教下去,直到他老得不能動(dòng)彈的時(shí)候。
|
編輯:
責(zé)編:
編審:
監(jiān)制: